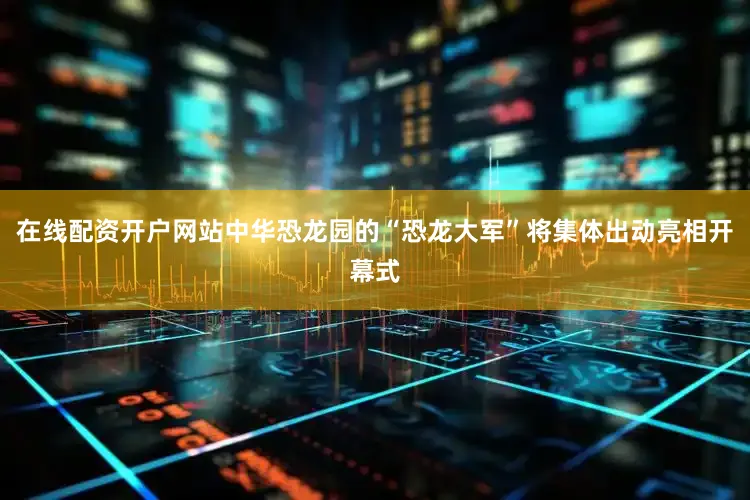房家夜宴喜雪,戏赠主人
白居易
风头向夜利如刀,赖此温炉软锦袍。桑落气薰珠翠暖,
柘枝声引管弦高。酒钩送醆推莲子,烛泪粘盘垒蒲萄。
不醉遣侬争散得,门前雪片似鹅毛。
观舞柘枝二首 之一
刘禹锡
山鸡临清镜,石燕赴遥津。何如上客会,长袖入华茵?
体轻似无骨,观者皆耸神。曲尽回身处,曾波犹注人。
白居易的《房家夜宴喜雪,戏赠主人》与刘禹锡的《观舞柘枝二首 之一》均以舞蹈为描写对象,但两首诗中舞蹈的意象与意义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审美取向与文化内涵。以下从舞蹈场景、功能指向及艺术表达三个维度展开比较分析:
一、舞蹈场景:私宴狂欢与公共展演的时空分野
展开剩余82%白居易诗中舞蹈:
诗作设定于“房家夜宴”的私人空间,雪夜闭门、围炉饮酒的封闭场景中,舞蹈是宴饮狂欢的组成部分。“柘枝声引管弦高”一句,仅以乐声高扬暗示舞蹈进行,未正面描写舞姿,而是将舞蹈融入酒酣耳热的整体氛围。烛泪粘盘、酒钩送盏的细节,更强化了舞蹈作为宴饮助兴工具的世俗性,其存在服务于“不醉遣侬争散得”的及时行乐逻辑。
刘禹锡诗中舞蹈:
刘禹锡则将柘枝舞置于“上客会”的公共展演场景中。“长袖入华茵”以俯视视角展现舞台,舞者成为视觉焦点。诗中“山鸡临清镜”“石燕赴遥津”的比喻,暗示舞蹈具有超脱日常的仪式感,舞者如山鸡对镜自赏、石燕凌空翱翔,其表演超越了私人宴饮的娱乐需求,成为一种艺术化的精神展示。
二、舞蹈功能:宴饮助兴与艺术观照的价值分野
白居易诗中舞蹈:
舞蹈在白诗中是宴饮链条中的一环,与“温炉软锦袍”“桑落气薰珠翠暖”等感官享受并列,共同构成雪夜纵欲的狂欢场景。诗人以“戏赠主人”为题,强调诗歌的戏谑功能,舞蹈在此被工具化,其意义仅限于烘托气氛、催动酒兴,如同“酒钩送醆”的酒令游戏,是宴饮流程中的标准化配件。
刘禹锡诗中舞蹈:
刘禹锡则以纯粹的艺术审美视角观照舞蹈。“体轻似无骨,观者皆耸神”直接点明舞蹈的审美震撼力,舞者身体成为艺术表达的媒介,其轻盈体态与观众“耸神”反应形成互动,构建起艺术创造与欣赏的双向关系。末句“
曲尽回身处,曾波犹注人”更以余波荡漾的视觉残留,暗示舞蹈超越时空的艺术生命力。
三、艺术表达:白描速写与意象凝练的技法分野
白居易诗中舞蹈:
白居易对舞蹈的描写采用白描手法,以“柘枝声引管弦高”一句带过,将笔墨集中于环境渲染与宴饮细节。舞蹈本身未被赋予独立审美价值,而是作为背景元素服务于全诗“雪夜狂欢”的主题。这种处理方式符合中唐诗歌“以文为诗”的世俗化倾向,舞蹈意象从属于整体生活场景的描绘。
刘禹锡诗中舞蹈:
刘禹锡则通过密集的意象群塑造舞蹈的神秘感。“山鸡临清镜”以自恋的禽鸟喻舞者对镜自赏的专注,“石燕赴遥津”以神话飞鸟象征舞蹈的超越性,两者共同构建出超现实的审美空间。“曾波犹注人”以水波荡漾比喻舞姿的余韵,将瞬间的动作转化为永恒的审美记忆,体现刘禹锡诗歌“以意象驱动叙事”的典型特征。
四、文化意涵:世俗享乐与精神超越的哲学分野
白居易诗中舞蹈:
白居易的舞蹈书写根植于中唐士大夫的享乐主义思潮。安史之乱后,文人群体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宴饮歌舞成为逃避现实的精神避难所。诗中“门前雪片似鹅毛”的严寒与“温炉软锦袍”的温暖形成对比,舞蹈在此是感官麻醉的手段,其意义被限定在“及时行乐”的生存哲学框架内。
刘禹锡诗中舞蹈:
刘禹锡的舞蹈书写则延续了盛唐诗歌的崇高美学。尽管身处贬谪境遇(此诗作于朗州司马任上),诗人仍通过柘枝舞的观赏实现精神超越。“何如上客会”的设问,暗示舞蹈具有连接世俗与理想的桥梁作用,舞者“长袖入华茵”的姿态,成为诗人对抗现实困境的精神投射。
结论
白居易与刘禹锡笔下的舞蹈,一者是世俗宴饮的狂欢符号,一者是艺术精神的具象化身。白诗中舞蹈消融于生活场景,成为及时行乐的注脚;刘诗中舞蹈独立于现实时空,升华为审美超越的载体。这种差异既源于两位诗人个性气质的不同(白居易之通达与刘禹锡之倔强),更折射出中唐诗歌从“生活化书写”向“艺术化沉思”的转型轨迹。舞蹈意象的分野,实为中唐文人精神世界分裂与重组的微观缩影。
发布于:河南省兴盛网-配资炒股之家-股票平台杠杆-怎么找配资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